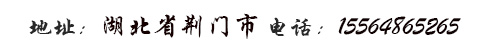迈耶middot夏皮罗描绘个人物品的
|
治疗白癜风哪里好啊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_7637171.html 为了阐明艺术是真理的一种敞开,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解释了凡高的一幅画[1]。 在区分存在的三种模式(即实用的器具、自然物和艺术作品)时,他谈到了此画。首先他想“不借助任何哲学理论地”来描述“……某种耳熟能详的器具——一双农鞋”;然后“为了便于在视觉上体现出来”,他选择了“凡高的一幅名画,而画家曾经数次描绘这样的鞋子”。但是,为了掌握“器具的器具性存在(theequipmentalbeingofequipment)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鞋子究竟是怎样物尽其用的”。对于农妇而言,鞋子怎么用是无需细想甚或看上一眼的。她穿着鞋站立或行走便知道了鞋的实用意义,而这是“器具的器具性存在得以落实”的地方。但是,要是我们只是想像一双普通的鞋子,或仅仅观照只是存在于绘画中的这双空荡荡的无人使用的鞋子,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找到真理中的器具的器具性存在的含义。我们在凡高的画中是无从知道这双鞋子置于何处的。除了一种不确定的空间围绕着这双鞋子之外,再无任何东西表明它们的所处与可能的归属。鞋子上甚至连地里的土块或路上的泥浆也不粘,而这些或许至少可以暗示鞋子的用途。仅仅只是一双农鞋而已,却又不仅如此。 在那黑糊糊的敞口中,鞋子磨损的内部赫然是劳动者步履的艰辛。在这硬邦邦、沉甸甸的鞋子上,聚集了她那迈动在寒风瑟瑟中一望无垠而又千篇一律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子的皮面上有着泥土的湿润。暮色将临,鞋底下悄悄流淌着田间小道上的孤寂。鞋子里回响着的是大地无言的呼唤,是大地对正在成熟中的谷物的悄然馈赠,是大地在冬闲荒芜田野里的神秘的自我选择,这一器具浸透了对有了面包后的无怨无艾的忧虑,弥漫了再次经受了匮乏的无言之喜,还有生命来临之前的颤抖以及来自四周的死亡威胁的战栗。这一器具属于大地,而且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护。正是出诸这种受保护的归属关系,此器具才跃而自持其身(resting-in-self)[2]。海德格尔教授知道,凡高画过好几幅这样的鞋子,但他却未鉴别自己所想到的这一幅,仿佛不同的画面是可以相互置换的,都呈现了同一的真理。想要把上述描述与原作或者照片作一比较的读者将在定夺哪一幅作品时颇感为难。凡高所画的八幅鞋子均被收录在德·拉·法耶(delaFaille)的目录里;此目录所收的全部作品在海德格尔撰写论文时都曾展出过[3]。其中只有三幅非常显然是针对哲学家的,显现了“鞋子磨损的内部那黑糊糊的敞口”[4]。它们明显是艺术家自己而非农民的鞋子的写照。它们有可能是他在荷兰时穿过的鞋子,但是这些画却是凡高-年间逗留巴黎期间画的,其中有一幅签了“87年”[5]。自从年前画过荷兰农民以后,凡高有两幅画鞋的作品——都是放在桌上其他物品旁边的一双干净的木底皮鞋[6]。后来,就如他在年8月写给他弟弟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在阿尔再现的“unepairedevieuxsouliers”(“一双破旧的皮鞋”),显然是他自己的鞋子[7]。第二幅描绘“vieuxsouliersdepaysan”(“一双破旧的农鞋”)的静物画曾经在年9月给画家埃米耶·博纳尔的信中提起过,但是此画缺少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种破旧的外表和黑糊糊的敞口的特征[8]。 在回信答复我的问题时,海德格尔教授爽快地告诉我,他所指的画就是在年3月阿姆斯特丹画展上看到的那一幅[9]。这显然是德·拉·法耶目录上第号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幅描绘三双鞋子的画,也许此画中有一只鞋底露出来的鞋子才是哲学家叙述中所指的鞋[10]。但是,依据上述这些或是其他的画,我们都无法恰如其分地说明凡高所画的鞋表达了一个农妇所穿的鞋子的存在或本质以及她与自然、劳动的关系。它们是艺术家的鞋,他当时是生活在城镇里的人。 海德格尔这样写道:“艺术品告诉我们真正的鞋子是什么。假如我们要认定,我们的那种作为主观行为的描述首先是想像一切而后又将之投射到绘画之中,那就是再糟糕不过的自我欺骗了。假如这里有什么令人生疑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在接触作品的过程中的体验太过贫乏,而对这种体验的表达又过于粗糙和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作品并不像初看上去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再现一件器具是什么样的,而是要反过来说,器具的器具性存在首先是通过作品,而且也仅仅是在作品中才获得了其外显的形态。”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在这作品中是什么在起作用呢?凡高的画是对真正的器具(即一双农鞋〉是什么的一种揭示。”[11] 天啊,哲学家本人就无疑是在自欺欺人了。他依然记得从接触凡高的油画时所获得的一系列有关农民和泥土的动人联想,而这些联想并非是绘画本身所支持的,反倒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那种对原始性和土地怀有浓重的哀愁情调的社会观基础之上的。他确实是“想像一切而后又将之投射到绘画之中”。在艺术品面前,他既体验太少又体验过度。 错误并不仅仅在于他以投射替代了对艺术品的真正细致的 难道海德格尔的错误就仅仅是对一个例子的错误选择吗?且让我们想像一下有一幅凡高所画的农妇的鞋。难道它就不会揭示海德格尔如此动情地描述过的那些性质以及与存在有关的天地吗? 海德格尔依然会遗漏掉绘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作品中艺术家的在场。在海德格尔对于绘画的描述里,他忽略了有关鞋的个人的以及相面术上的(physiognomic)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鞋子变成了艺术家眼中如此具有魅力的主题(且不论特定色调、形式和作为绘画作品画面的笔触之间的密切关联)。当凡高描绘农民的木底皮鞋时,他将它们明确地画成没有磨损的样子,而且其表面就像是在同一桌子上他放在鞋子旁边的其他静物一样光洁,诸如碗和瓶子等。在后来描绘农民的皮制拖鞋时,他就让其背向观众了[13]。他自己的鞋是孤单单地放在地上的,他把它们画得仿佛是面对着我们,而且由于是如此个性化和皱皱巴巴,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有关一双老态龙钟的鞋的真实肖像。 我认为,我们已经是颇为接近凡高对这双鞋的感受了:这种感受一如克努特·哈姆森(KnutHamsum)在其19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饥饿》的一个片断中对自己的鞋所做的描写:“由于我以前从未细看过自己的鞋子,于是开始审视它们的外观与特征,而当我活动脚的时候,鞋子的外形以及破旧的鞋帮也就动了起来。我发现鞋子上的皱痕和白色的接缝获得了一种表情——也就是说,给了鞋子以一种脸的特征。我的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已融入到了鞋子里:它们就像我的另一自我的魂灵一样影响着我——是我的自性之中有血有肉的一个部分。”[14] 将凡高的画与哈姆森的文本予以比较,我们就是以一种异于海德格尔的方式来阐释艺术家的画了。哲学家在描绘鞋子的画作中发现了一种有关农民不加反思地居于其间的世界的真理;哈姆森则将真实的鞋子看成是既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鞋的使用者,同时又是作家的人的体验对象。哈姆森的个性属于那种深思的、自律的漂流者,较诸农民更接近凡高的处境。不过,凡高在某些方面也和农民有相似之处;作为艺术家而创作时,他坚持不懈地从事某一种事情;在他看来那是无可逃避的呼唤、他的生命。当然和哈姆森一样,凡高也具有超凡的再现才华;他能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力量将事物的形式与品质挪移到画布上去;但这些都是他深有感触的事物,在这里,就是他自己的鞋子——它们与他的身体不可分离,也在重新激起他自我意识时而无以忘怀。它们同样是被客观地重现于眼前的,仿佛赋予了他种种感触,同时又是对其自身的幻想。他将自己的旧鞋孤零零地置于画布上,让它们朝向观者;他是以自画像的角度来描绘鞋子的,它们是人踩在大地上时的装束的一部分,也由此能让人在找出走动时的紧张、疲惫、压力与沉重——站立在大地上的身体的负担。它们标出了人在地球上的一种无可逃避的位置。“穿着某人的一双鞋”,也就是处于某人的生活处境或位置上。一个画家将自己的旧鞋作为画的主题加以再现,对他来说,也就是表现了一种他对自身社会存在之归宿的系念。虽然在田间作画的风景画家会和户外的农民的生活有些相同之处,但是,凡高的迷人主题就是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哈姆森语)的鞋子;它们不只是实用的物品了。 年曾与凡高一起在阿尔住过的高更就感受到了朋友描绘鞋子的画背后的个人轨迹。他在回忆凡高时讲了一则与后者的鞋有关联的感人故事。 “画室里有一双敲了大平头钉的鞋子,破旧不堪,沾满泥土;他为鞋子画了一幅出手不凡的静物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件老掉牙的东西背后的来历疑惑不定,有一天便鼓足勇气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要毕恭毕敬地保存一件通常人们会当破烂扔出去的东西。” “‘我父亲,’”他说,“‘是一位牧师,而且他要我研究神学,以便为我将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我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动身去了比利时,我要到厂矿去传播福音,倒不是别人教我这么做,而是我自己这样理解的。就像你看到的一样,这双鞋子无畏地经历了那次千辛万苦的旅行。’” “在给波兰纳杰的矿工布道的日子里,温森特承担了对一个煤矿火灾受害者的护理。此人在烈火中严重伤残,所以,医生对其康复已失去了信心。他想,惟有奇迹方能救活这个人。凡高充满爱意地照顾他,而且救了这个矿工的命。” “‘离开比利时之前,我站在那个人面前——他的眉宇间伤疤累累,仿佛是荆棘编成的王冠,他俨然是复活的基督。’” 高更继续道:“温森特再次拿起调色板;他默默地工作。他身旁是白色的画布。我开始画他的肖像。我也仿佛看到了一个基督正在传播仁慈与谦恭。”[15] 我们不清楚高更在阿尔所见的那幅只画了一双鞋子的作品是哪一件。他把画描述成紫罗兰色调,与画室的黄墙构成了对比。这无关紧要。尽管是数年之后才写的,而且还有某些文学味,但是高更讲述的故事证实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凡高来说,鞋是其自身生命中的一部分。 注释:[1]M.海德格尔,‘DerUrsprungdesKunstwerkes’(《艺术作品的本源》)收入Holzwege(《林中路》,法兰克福,年。书重印时,由H.G.伽达默尔作序论,斯图加特,年);A.霍夫施塔特(A.Hofstadter)译作《一件艺术品的本源》,收入霍夫施塔特和R.库恩斯(R.Kuhns),《艺术和美的哲学》(纽约,年),第-页。正是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Goldstein)最先叫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pif.com/qpzp/11390.html
- 上一篇文章: 轻松学名方释义第32讲小续命
- 下一篇文章: 针灸医案丨针刺速效医案13则外伤荨麻